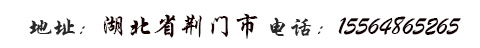连载白石老人自述诗画篆刻渐渐成名4
|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我三十七岁。正月张仲飏介绍我去拜见王湘绮先生,我拿了我作的诗文,写的字,画的画,刻的印章,请他评阅。湘公说:“你画的画,刻的印章,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哪!”湘公说的寄禅,是我们湘潭有名的一个和尚,俗家姓黄,原名读山,是宋朝黄山谷的后裔,出家后,法名敬安,寄禅是他的法号,他又自号为八指头陀。他也是少年寒苦,自己发愤成名,湘公把他来比我,真是抬举我了。 那时湘公的名声很大,一般趋势好名的人,都想列入门墙,递上一个门生帖子,就算作王门弟子,在人前卖弄卖弄,觉得很有光彩了。张仲飏屡次劝我拜湘公的门,我怕人家说我标榜,迟迟没有答应。湘公见我这人很奇怪,说高傲不像高傲,说趋附又不肯趋附,简直莫名其所以然。曾对吴劭之说:“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我门下有铜匠衡阳人曾招吉,铁匠我同县乌石寨人张仲飏,还有一个同县的木匠,也是非常好学的,却始终不肯做我的门生。”这话给张仲飏听到了,特来告诉我,并说:“王老师这样地看重你,还不去拜门?人家求都求不到,你难道是招也招不来吗?”我本也感激湘公的一番厚意,不敢再固执,到了十月十八日,就同了仲飏,到湘公那里,正式拜门。但我终觉得自己学问太浅,老怕人家说我拜入王门,是想抬高身份,所以在人面前,不敢把湘绮师挂在嘴边。不过我心里头,对湘绮师是感佩得五体投地的。仲飏又对我说:“湘绮师评你的文,倒还像个样子,诗却成了《红楼梦》里呆霸王薛蟠的一体了。”这句话真是说着我的毛病了。我作的诗,完全写我心里头要说的话,没有在字面上修饰过,自己看来,也有点呆霸王那样的味儿哪! 那时,黎铁安又介绍我到长沙省城里,给茶陵州的著名绅士谭氏三兄弟,刻他们的收藏印记。这三位都是谭钟麟的公子。谭钟麟做过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是赫赫有名的一品大员。他们三兄弟,大的叫谭延闿,号组安;次的叫谭恩闿号组庚;小的叫谭泽闿,号组同,又号瓶斋。我一共给他们刻了十多方印章,自己看着,倒还过得去,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却有一个丁拔贡,名叫可钧的,自称是个金石家,指斥我的刀法太烂,说了不少坏话。谭氏兄弟那时对于刻印,还不十分内行,听了丁拔贡的话,以耳代目,就把我刻的字,统都磨掉,另请这位丁拔贡去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想:我和丁可钧,都是摹仿丁龙泓、黄小松两家的,走的是同一条路,难道说,他刻得对,我就不对了么?究竟谁对谁不对,懂得此道的人自有公论,我又何必跟他计较,也就付之一笑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我三十八岁。湘潭县城内,住着一位江西盐商,是个大财主。他逛了一次衡山七十二峰,以为这是天下第一胜景,想请人画个南岳全图,作为他游山的纪念。朋友介绍我去应征,我很经意地画成六尺中堂十二幅。我为了凑合盐商的意思,着色特别浓重,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用了二斤,这真是一个笑柄。盐商看了,却是十分满意,送了我三百二十两银子。这三百二十两,在那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人家听了,吐吐舌头说:“这还了得,画画真可以发财啦!”因为这一次画,我得了这样的高价,传遍了湘潭附近各县,从此我卖画的声名,就大了起来,生意也就益发地多了。 我住的星斗塘老屋,房子本来很小,这几年,家里添了好多人口,显得更见狭窄了。我拿回了三百二十两银子,就想另外找一所住房,恰巧离白石铺不远的狮子口,在莲花寨下面,有所梅公祠,附近还有几十亩祠堂的祭田,正在招人典租,索价八百两银子,我很想把它承典过来,只是没有这些银子。我有一个朋友,是种田的,他愿意典祠堂的祭田,于是我出三百二十两,典住祠堂房屋,他出四百八十两,典种祠堂祭田。事情办妥,我就同了我妻陈春君,带着我们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搬到梅公祠去住了。莲花砦离余霞岭,有二十来里地,一望都是梅花,我把住的梅花祠,取名百梅书屋。我作过一首诗,说: 最关情是旧移家,屋角寒风香径斜。 二十里中三尺雪,余霞双屐到莲花。 梅公祠边,梅花之外,还有很多木芙蓉,花开时好像铺着一大片锦绣,好看得很。我定居北京以后,回想那时的故居,也曾题过一首诗: 千年不到莲花洞,草木余情有梦通。 晨露替人垂别泪,百梅祠外木芙蓉。 梅公祠内,有一点空地,我添盖了一间书房,取名借山吟馆。房前屋后,种了几株芭蕉,到了夏天,绿荫铺阶,凉生几栩,尤其是秋风夜雨,潇潇簌簌,助人诗思。我有句云: 连花山下窗前绿,犹有挑灯雨后思。 这一年我在借山吟馆里,读书学诗,作的诗,竟有几百首之多。 梅公祠离星斗塘,不过五里来地,并不太远。我和春君,常常回到星斗塘去看望祖母和我父亲母亲,他们也常到梅公祠来玩儿。从梅公祠到星斗塘,沿路水塘内,种的都是荷花,到花盛开之时,在塘边行走,一路香风,沁人心胸。我有两句诗说: 五里新荷田上路,百梅祠到杏花村。 我在梅公祠门前的水塘内,也种了不少荷花,夏末秋初,结的莲蓬很多,在塘边用稻草盖了一个棚子,嘱咐我两个儿子,轮流看守。那年,我大儿子良元,年十二岁,次儿良黼,年六岁。他们兄弟俩,平常日子,到山上去砍柴,砍柴挺卖力气,我见了心里很喜欢。有一天,中午刚过,我到门前塘边闲步,只见良黼躺在草棚之下,睡得正香。草棚是很小的,遮不了他整个身体,棚子顶上盖的稻草,又极稀薄,他穿了一件破旧的短衣,汗出的像流水一样。我看看地上的草,都给太阳晒的枯了。心想,他小小年纪,在这毒烈的太阳底下,怎么能受得了呢?就叫他道:“良黼,你睡着了吗?”他从睡梦中曜地坐了起来,怕我责备,擦了擦眼泪,对我看看,喘着气,咳嗽了一声。我看他怪可怜的,就叫他跟我进屋去,这孩子真是老实极了。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我三十九岁。朋友问我:“你的借山吟馆,取了(借山)两字,是什么意思?”我说:“意思很明白,山不是我所有,我不过借来娱目而已!”我就画了一幅《借山吟馆图》,留作纪念。有人介绍我到湘潭县城里,给内阁中书李家画像。这位李小书,名叫镇藩,号翰屏,是个傲慢自大的人,向来是谁都看不起的,不料他一见我面,却谈得非常之好,而且还彬彬有礼。我倒有点奇怪了,以为这样一个有名的狂士,怎么能够跟我交上朋友了呢?经过打听,原来他有个内阁中书的同事,是湘绮师的内弟蔡枚功,名毓春,曾经对他说过:“国有颜子而不知,深以为耻。”蔡公这样地抬举我,李翰屏也就对我另眼相看了。 那年十二月十九日,我遭逢了一件大不幸的事情,我祖母马孺人故去了。我小时候,她背了我下地做活,在穷苦无奈之时,她宁可自己饿着肚子,留了东西给我吃,想起了以前种种情景,心里头真是痛如刀割。 上一篇:连载白石老人自述——诗画篆刻渐渐成名(3)下一篇:白石老人自述——五出五归(1)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a.com/mfrzw/9440.html
- 上一篇文章: 海马体秋季花颜照全新推出,演绎巾帼侠气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