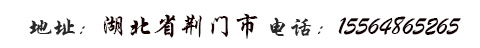刘晓村丨城上芙蓉锦绣舒我与成都二
|
北京专业荨麻疹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zhiliao/210116/8595950.html 『读书、喝茶、沙龙、小住,繁华静处遇知音』 刘晓村:年生于成都,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先后供职于四川作家协会、中央戏剧学院。著有长篇小说《蚀城》(作家出版社)《幸福还未到来》(作家出版社),担任多部影视剧编剧、文学策划,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人物专访等文章逾百万字。 城上芙蓉锦绣舒——我与成都(一) 文丨刘晓村 1 年,我分到四川作家协会《星星诗刊》当了一名编辑。主编是位著名诗人,写作特别勤奋。他思维开阔活跃,诗作丰沛。他对编辑们很宽容,希望大家都能在工作之余坚持创作。我们编辑部的同仁,年龄都比我大得多。他们都曾做过多种职业,阅历不凡,几乎都是四川乃至全国有名的诗人。我能在这样的小环境中工作,算是初入社会的一大幸运。 我喜欢诗人们处处流露的真性情,尤为欣赏他们玄妙落拓奇幻的想象力。做一个诗歌编辑,竟然能接触到如此深广的社会层面,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年代,不安于世俗生活的人都要写诗。我的作者涵盖了一切职业,他们的数量极其庞大:工人、农民、解放军、商人、公务员、医生、警察、售货员、工程师、教师、记者……每一天,我们编辑部的来稿都有一大麻袋之多。 当我早晨走出电梯,瞧见一个挑着扁担的农民坐我办公室门口,亲自把他写作很久的诗稿交到我手上,然后再去市场卖菜;或是一位房管局的干部,在投稿的诗歌中附上几句给编辑的话,说他在每天下班之后,会留在办公室写诗。写诗的夜晚,他才感到自己仍然活着……这些时刻,这些诗人,他们无形中在帮助迷茫的我重新定位。 2 成都就是这样,本性热闹泼辣,它的生活触须伸得特别长,细节或许平淡,质地却相当丰富。“眼前兴废事,烟水又黄昏”,龙门阵摆将起来,“三花”谈(三花:成都出产的茉莉花茶。谈三花:意为聊天)不完。何况,其时我不过22岁,青春期健旺的生命力,最容易被健忘、好奇、轻信、热情、冲动、创造等内容填满。借助有意无意的认知,借助各种诱惑,我羞羞答答、欲拒还迎、跃跃欲试、边干边怨、边怨边干地渐渐贴近、走进和渗透进了在成都的日子…… 那几年,我特别地无所事事,上没老(爸妈还算中年),下没小(单身汉),没有职称,没有资历,没有钱,没有前途……我们编辑部每天只上半天班,下午和晚上,我和几个同学或发小混在一起,骑着自行车,东晃西荡,游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我们吃遍了味道巴适又负担得起的渣渣馆子和路边摊。火锅粉配八宝粥的吃法刚刚流行,我们都已经吃腻了;贺水饺、蒋排骨、雨田小馆、华兴煎蛋面、滇味米线、王梅麻辣烫、白家肥肠粉……轮换着吃。当然,我们不得去啥子“龙抄手”“陈麻婆”“老妈火锅”之类的地方,那些名吃都是麻外地人的……我很少在家吃饭,到了月底发工资前,就要找妈妈借钱打救济。 我从来没有涉足过这么多地方:昔日的公馆,规整的、单位接收的大四合院,市民居住的大杂院、小杂院,大单位的家属院,烂单位的家属院,高干居住区,危房,钉子院,刚刚兴起的别墅区,高档公寓区,涉外公寓……在成都工作的这5年间,我与各阶层的人都有或深或浅的接触。我并没有什么深入生活、观察人间的观念,按照妈妈的话说,我只是太贪耍了,每天一睁眼,想的就是今天该怎么耍!以张爱玲剖析她自己的方式来形容我的状态的话,或许就是“一个缺乏生活的人,她对生活是贪心的。” 我每天上下班,都要骑自行车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广场中心四川省展览馆的位置,从前是成都的老皇城。它近似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只是规模小得多。老皇城在上世纪60年代初拆除,这个地方还是成都的心脏地段。广场中心的领袖塑像下挂着巨幅标语:“建设国际大都市”,我看着这个标语,简直五味杂陈。“少不入川,老不出川”,并非陈腐过时的老话,时间的轮盘已经转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所谓时代的新人,成都的和全国的都一样,他们纷纷奔去了广东、深圳和海南等地方…… 3 写作并没有中断,虽然速度缓慢。 年,我写作的诗歌、散文和艺术评论陆续在各地发表。写作过程本身比发表更让我兴奋。我曾严重担心的境况似乎并未出现:回到成都之后,可能会丧失对艺术的兴趣和热情。事实上,我和大学同窗好友(她未能如愿分到广东,被迫来到成都)一起,我们彼此不断相互提醒,一定要保持对艺术的激情,保持敏锐的感受力,别被当地的风气同化。她在电视台做导演,精力过人,干劲十足。她拉上我,我们一起替电视台策划节目,写剧本。我们与广播电台合作,做诗歌朗诵会。我们还替杂志写作剧评,对成都的各种有意思的艺术活动更是趋之若鹜……在成都的日子,我反倒是前所未有地接地气。日复一日,自然就被地底的根须所紧紧缠绕。 然而,有谙熟的上海作为参照,我清楚地看到成都在方方面面的局限性。即便是在文化界,自满自得、故步自封、打压新人新事的人仍然不少。偶尔,我去参加官方的会议,会上那些专家对本地文化和彼此的吹捧程度让人咋舌。有时,某些人知道我毕业于上海的艺术院校,又不会违心奉承他们,就会对我冷嘲热讽。并非他们对我有何成见,我们并不熟悉,那只不过是他们的习惯。我在上海和北京的许多老师,他们才高八斗,却都谦逊低调,保持着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多是真诚地给予鼓励。对比之下,我时常哭笑不得,也感觉相当憋闷。 4 写作步入了它匀速不断的轨道。 那几年,我的散文被几部文集收录,戏剧小品和随笔也分别在上海的成都获奖,长篇小说也已经完稿。最让我兴奋的是,我居然被我崇拜的四川美术学院78级的12位画家选定为他们新成立的“78艺术工作室”的艺术总监。这些画家都是四川美术界艺术本体意义上的创作中坚,基本游离于官方的主题性绘画圈之外。我看着他们的素描、写生、油画、连环画、书籍装帧等作品长大,许多人的名字我早就如雷贯耳,只是还不熟悉本人。 中学时期,我特别熟悉并喜欢“伤痕文学”、“伤痕美术”、“伤痕电影”等文学艺术。我比这批创作“伤痕艺术”的作家艺术家基本小一轮。我没有当过知青,也缺乏对农村生活的深入了解,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代,我颇为仰慕那些“吃过苦”的作家艺术家。 我只有25岁,按说这批画家认识不少很有份量的美术评论家,他们并不非选用我来做他们的艺术总监。大概是他们喜欢年轻人的单纯真诚,又与我艺术观念合拍,性情相投。总之,我们合作得特别默契。我为他们的画展写前言,为他们的作品写评论,长时间地处于创作的亢奋状态。 那时候,他们几乎都还不到40岁,正值创造力的高峰时期。他们开朗热情,洒脱坦直,幽默得不得了,特别会讲噻话(噻话:成都方言,意为不正统的话)。大家凑在一起工作或玩耍的时候,我总是从头笑到尾,特别地开心……年、年,我们连续在四川美术馆举办了两届油画展,观众很多,反响也好。 写作的路子似乎更宽阔了,我脱离了生涩的学生气,对未来的创作逐渐拥有了些许自信。 5 年,我认识了丈夫。他是北京人,又是单亲独子,让他离开北京到成都去工作生活,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我去北京似乎更为天经地义,被大多数人看作是“积极向上”的幸事。我虽不很情愿离开成都,却也只能服从感情的选择。偶尔,我会觉得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和捉弄,在我特别想要去北京工作时,万门紧闭;待我在成都有了越来越多朋友,工作也更加顺手,单位连住房都分给我了,我真正不想再离开成都之时,还不得不去北京定居。 然而,心理意义上的移居却一直未能彻底完成。调到北京工作后,长达数年间,我的大脑经常是一片空白,任何东西都写不出来,如何焦虑也没用。如果我调入的不是北京的高校,而是某个没有寒暑假的单位,以我年轻软弱、依赖性强的个性,也许我会屈从于与北京的朝夕相处。假以时日,我会从依赖北京,继而依恋上北京。只能说是命中注定,我和成都的缘分,倒是因为我在大学工作的便利,依然紧密相连。 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在放假的第二天,迫不及待地回到成都。20年来,只有年没有回成都。冬天,爸爸妈妈来北京过年了;夏天,我带着女儿去了美国。有天,有个成都朋友在电话中给我描述成都因为修地铁而极其混乱的路况,我对此话题的反应却引来朋友的嘲笑,她说:“你就像很久没有回过成都一样,就是一年而已嘛。” 6 旅游手册上这样描述成都:位于四川省中部,四川盆地西部,总面积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87平方公里。东西长公里,南北宽公里。全市·39万人,市区·47万人。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四川省经济文化中心…… 历史上,五代后蜀时期,后蜀主孟昶命人在成都城上遍植木芙蓉,每到秋季,五色芙蓉竞相开放,成都因有“芙蓉城”之名,简称“蓉城”。 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印刷体或特别诗意地来感知我们身居其中的城市。我们只知道城市在不断变大,一环、二环、二点五环、三环……朋友们的家相距越来越远,大家来往起来也没有从前方便。我们会感觉城市密度越来越大,即使是穷街陋巷或已过午夜时分,大街小巷依然到处都是行人。我们感叹人口流动迁徙的数量变得频繁,大街上甚至已经难得听到本市土族的口音…… 成都自建城起,2千多年来,从没改换过名字。虽然建城历史悠久,成都却是个很小的城市,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小时的自行车程就可以横穿全城。 成都在这些年变成了既热门又被人看轻的城市,像是个城市的鸡肋:在北京上海广东甚至国外生活工作得疲惫了,成都让人想念;在外地意气风发的时候,成都就是西部地区观念滞后、盆地意识浓重、缺少发展机会的城市。那些即将考大学的莘莘学子,还是把离开成都到北京上海等地方读书,看作是有抱负的行为…… 成都似乎自古就充当着这样尴尬而带有治愈色彩的角色,从杨雄王勃到陆游杜甫,从郭沫若到巴金,从汪曾祺到罗念生,不管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文化名流们在成都留下了他们一生中最美的诗篇和难忘的生活,然而,偏安一隅,从他们的文章中依然可以看到,他们在成都的生活基调,往往洇染着诸多的被迫和无奈。只要时局平稳或个人有发展机会,他们就会毅然离开这里。毕竟,成都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它自身文化底蕴深厚,但与中国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流观念很有些距离。 7 20多年来,我缺乏在成都的日常生活经验,无法像老成都人那样时时凝视它,天天感受它,无法随时抓取它最动人的细节和最细腻的变化;我也不像那些旅游者,踏上成都的地界,带着听来的一点传说,个人的一点偏见,获得的一点印象,然后做出一番结论。这结论即便是以偏概全,也非常的理直气壮。 当我提笔写成都的时候,一时竟有些无从说起。毕竟,太多诗人、作家、艺术家和普通人都写过成都,其中不乏精彩之作。我很喜欢看这类文章,从初期狼吞虎咽地看,到现在有所选择地看,看了一本又一本,一篇又一篇。成都,单就其在笔墨下的形象,似乎已被穷尽。 我推翻了之前写的好几稿,总是感到不满意。我写的成都从各个方面、以各种角度似乎都被人写过,并且大家都比我写得全面深邃透彻。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在谈到读者和作者身份转换的关系时,有这么一番话(大意):要写的一切都已经被写过,我只好做个读者。直到某一天,我觉得我即将要写的,似乎还未被写,于是,我提起了笔……那好吧,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到起点,从在成都的经历写起,梳理一下成都与我、我与成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德国评论家本雅明认为,外人看一座城市的时候,感兴趣的是异国情调或美景。而对当地人来说,其联系始终掺杂着回忆…… 虽说是回忆,我并不认为它完全属实。尽管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但落在纸上的文字,只要不是录音记录整理,总会含有想象的成分。在企图还原历史遗迹的同时,我们的记忆、认知、情感、写作风格、写作技巧等等因素,都会使文章内容部分“变形”。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其杰作《伊斯坦布尔》里说:“对回忆录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事实叙述的准确与否,而是前后是否呼应。”好在,再现并非我的目的,表现才是终极使命。我想要让读者看到的内容,更是我想说给自己听的絮语…… 初稿于年3月、7月 修订于年2月、8月 作家·刘晓村丨专栏 1.成为一个作家 2.胡同里的人们,悲欢离合 3.编辑部的一段往事,回忆小黎 4.每个人都有回家的路,你我终将告别 5.诗人们迸发的每一首诗,都是这个城市闪耀的荣光 6.下乡的故事丨说不上经了风雨,但长了见识 7.《苏珊和老虎》丨感受英国儿童教育中的人性化、低调、日常、温暖 8.童年没有玩伴的孩子,长大了会忧郁 9.一个人有着怎样的童年,长大后就会有什么样的情感方式 10.从孩子的眼里,看见了原谅 11.再也没能见到,那个比鲜花更漂亮的种花人 12.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充满善意 13.埃文河畔,宁静的土地上埋葬着伟大的灵魂——莎士比亚 14.在英国女王的住所温莎城堡,见识大家风范 15.霍沃斯,因勃朗特三姐妹而不朽 16.牛津是大学中有城市,剑桥是城市中有大学 17.在青春的荷尔蒙和节日的氛围中,总会陷入一种迷乱的情感 18.所有人都是快乐的,惟独我在外 19.全部的戏剧,多于全部的生活 20.印象上海,既浪漫又虚无的感觉 21.上海的地气,浸润在城市丝丝缕缕中 22.走出四川,印象上海 23.未被真正占领的青春,异常动人…… 24.一个人喜欢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表达 25.有个人在记忆里,他永远年轻、清秀、干净 26.故人已逝,惟愿斯文儒雅,获得终极幸福 27.刘晓村丨时而勤奋痴迷,时而狂放不羁 28.刘晓村丨我们活着的人,也还是孤独的 29.刘晓村丨张荷花(一) 30.刘晓村丨张荷花(二) 31.刘晓村丨张荷花(三) 32.刘晓村丨冯国祥(一) 33.刘晓村丨冯国祥(二) 34.刘晓村丨《羊道》:马陷落沼泽,心流浪天堂 35.刘晓村丨乘车记(一) 36.刘晓村丨乘车记(二) 37.刘晓村丨乘车记(三) 38.刘晓村丨我的艺术家朋友之一:甘庭俭印象 39.刘晓村丨画布前的独行者:荷译印象 40.刘晓村丨在时间的激流外——冯大庆印象 41.刘晓村丨帕慕克的爱情博物馆——读《纯真博物馆》 42.刘晓村丨见书形如晤面——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 43.刘晓村丨几部外国小说 44.刘晓村丨刘晓村丨科塔萨尔短篇小说集《万火归一》 45.刘晓村丨戏剧人生——罗大军印象 46.刘晓村丨爱就爱了,又怎么样? 47.刘晓村丨爱了就爱了,又怎么样?(续编) 48.刘晓村丨逆光(一) 49.刘晓村丨逆光(二) 50.刘晓村丨逆光(三) 51.刘晓村丨逆光(四) 52.刘晓村丨逆光(五) 53.刘晓村丨城上芙蓉锦绣舒——我与成都(一) —FIN— 文丨刘晓村 排版丨慢师傅 编辑丨WEYLEAN 刘晓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a.com/mfrjz/8198.html
- 上一篇文章: 东风菜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