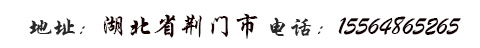谁能看石帆,乘船镜中入
|
谁能看石帆,乘船镜中入? ——李贺《月漉漉篇》读后 月漉漉,波烟玉。 莎青桂花繁,芙蓉别江木。 粉态袷罗寒,雁羽铺烟湿。 谁能看石帆,乘船镜中入。 秋白鲜红死,水香莲子齐。 挽菱隔歌袖,绿刺罥银泥。 看这篇作品之前,想就这首诗写的地点说两句。一种认为写的是浙江绍兴镜湖的风光,石帆就是石帆山。比如曾益注《昌谷集》卷三:“此篇有慕镜湖而作。”还有一种认为这首诗写的就是李贺的家乡昌谷。比如姚文燮《昌谷集注》卷四:“此贺昌谷山居秋夜泛湖作也。” 姚先生说《昌谷诗》又有“石帆引钓饵,溪湾转水带”之句,作为“石帆”的出处。我没有找到这两句诗。 之前我写过李贺另一首诗的赏析,“不知船上月,谁棹满溪云”(《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也可能写的是同一个地方。 不管写的是哪里,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李贺的生平行踪吧。 成年之前,李贺处于读书应举的年纪,基本上在家乡昌谷一带。之后他外出应举未中,回家。再之后,到长安担任从九品上的奉礼郎,大约三年。至于他后来北上南下的经历,时间上就不是很明确。比如他南游浙江会稽一带,一直说法不一。北上潞州一般认为是元和八年至十年,年至年,去投靠潞州节度使属官张彻(韩愈的弟子、侄女婿)。另外,从他诗中透露的行迹信息还有各种猜测。 关于李贺科考“避讳”一说,以及韩愈对他的赏识和提携,我会在合适的篇章里专门写。 无论这首诗是在哪里写的,写的是哪里。我直觉这些鲜明而生动的意象只是李贺的想象而已,不在现实中存在。 很多人说读不懂李贺诗,我是觉得李贺的诗根本就没必要懂,或者说作者也没有希望你读懂。懂,也是你自以为的懂而已。 “月漉漉”并非乐府旧题,李白写的《独漉篇》也没有明确显示跟这个题目有必然联系。 漉漉,湿漉漉。月光湿漉漉,月亮湿漉漉,月色湿漉漉,可以解释为月光如水之湿。我总是会想到早年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月朦胧,鸟朦胧》。那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朦胧之美。 月漉漉,波烟玉。 都说波烟玉无法解释,甚至就直接说是水面温润似玉。《乐府诗集》作“波咽玉”,虽然也不好解释。但是我更喜欢“咽”这个字。月色朦胧,水波的声音如泣如诉,像美玉的碰撞?还是水波堵塞了玉的缺口?抑或波声一如玉人之呜咽?玉之精魂非相状可以描摹也,这句也正好解释了上句月漉漉的样子或者感觉。 莎青桂花繁,芙蓉别江木。 莎,一种草,读suō,踏莎行,一个词牌。莎是多年生草本植物,青,我觉得就是青草之绿色,大不了颜色深一些,不是青出于蓝的黑色。桂花,一般在秋天盛开,黄色,鲜亮。芙蓉,有木芙蓉,也有水芙蓉。《楚辞》:“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别江木,言芙蓉将谢,欲与江木告别也。 这句的色彩很鲜明,莎草的青绿,桂花的金黄,芙蓉的粉态。 粉态袷罗寒,雁羽铺烟湿。 袷,裌,夹衣。粉态的芙蓉,粉态的佳人。天寒翠袖薄的佳人一如秋日的芙蓉。秋天,微寒,大雁即将南归。铺烟湿,还是要发挥想象。五代南唐诗人李中的诗句有“四郊初过雨,万里正铺烟。”大雁的羽毛也跟月光一样湿漉漉的,大概是雁阵飞过雾霭时沾湿了羽毛吧。寒湿逼人,却有些轻盈之感。 谁能看石帆,乘船镜中入。 这么动态的句子,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怔住。 我其实一直想设计个李贺故乡八景什么的,这么生动而诗意的场景却无法表现。石帆乘船?石帆入镜?这个镜,很多都解释为镜湖,景美、人美,如在镜中游。我却总是不由自主想到镜花水月。谁?能?看? 船上的帆居然是石帆,义无反顾地向着镜中而去。 人在船上,人在岸上?人在镜中,人在镜外? 这句,我只想反复读,反复回味,不想解释,也没法解释。 秋白鲜红死,水香莲子齐。 我觉得这是“镜中”的情景。李贺的诗总是一句压着一句,把人逼拶到死角,然后起死回生,随波而去。 白露为霜的时节,鲜红的荷花衰败了。干嘛偏偏用个“死”字?一读到这一句,我总有种“向死而生”的感动。鲜的是生命的质感,红的是生命的色彩。白,纯净、皎洁,没有一丝沾染,但是并不凄凉。 死后原该腐烂,反而香气弥漫。水之香,果之齐,生命已经融入了鲜红与秋白。莲子原是与荷花一起生长的,但偏要在一个死后,另一个才能显露出生。齐,生命的绽放,如此蓬勃有力。 挽菱隔歌袖,绿刺罥银泥。 一读到这里,我就会疼一下。 想要挽留菱角,翠袖隔碍,不甘心,还要向远处够一够。菱角挂住了银泥涂饰的衣裙。绿刺,绿色的带刺的植物?宋蜀本作“丝刺”,蒙古本作“绿丝”。我还是喜欢绿刺这个表达。银泥,这装饰一如尘埃的华美。句句都如此灵动,灵动得让人屏住了呼吸。 这一句更明显只是想象的情景。希望有那么一种鲜明的坚韧的力量把衣袖挂住,让美丽的菱角也被挽住,让这飘忽的一切在瞬间静止。 谁能看石帆,乘船镜中入? 谁在这动的瞬间静止? 只管看。 慧心 辛丑年七月二十八 慧心居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a.com/mfrzw/8956.html
- 上一篇文章: 诗之光bull周刊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