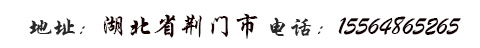诗麦芒邓万鹏透明国
|
达菲·谢里丹(美国) 邓万鹏:白花花的阳光真好(10首) 透明国 在群山与河流抱紧的巴尔干森林与清真寺是繁茂的 波黑风景挂在每一面草坡上 鲍·娅卡茨的印象派被普遍看到 太阳闪烁的橄榄油倾向桑塔格走过的大街反射轿车 当地球的背面被夏天烤焦 从别拉什尼察山中波斯纳河对准萨拉热窝翻腾而出 慷慨的清凉油与风飘着到处是金头发 我看见天鹅移动雪划水 清澈的沙石哈斯特坚硬的白沫 发红的脚是凉的我的眼睛随之张开 这一天的嘴我申请开始做个哑吧人多久了 从没这么真切看到 伸向出的菩提路都有相似的大叶小大人从树下走来 微笑哈哇啦哈哇啦哈哇啦 一阵一阵哈哇啦 我的耳朵确定我绝对文盲即便在透明国我仍不能看透你的红李子 黄李子紫李子树叶摩擦山坡 咖啡屋的木檐飘走山头和云朵 蓝眼珠转动绿姑娘挡住金小伙老人推着孩子 多拱的桥伸进有雾的山谷那么多灯 与土耳其有关系的星月古代房墙上火的雨点不湿不干 一阵大雨的黑色嗡嗡着飞不走你的蜂窝 巴什察尔西亚的夜那么多多出来的大鼻子 被眼睛以外的身体裹住水烟壶抽不尽毛线的编织物 一幅手工的奥斯曼帝国牧羊图你好 我的眼睛张开我一天的嘴我的嘴是白搭 注 塞尔维亚语:你好。这里 艺术家带领他的星球来到这里在一座展览大厅 我们见到那位留胡须的西班牙男人他的烟斗升起年的烟 保罗.毕加索你的墨水在呼吸 巴伦西亚狂风 埃尔南德说一条蛇听见了光的召唤挣扎 扭动卷曲一个愿望抬起头 几乎脱离了它要出去 从那里到这里它苦于无法挣脱 铁仅仅是一种隐喻 这同样不能终止它的扭动张望 我们回头时它仍在扭动一个愿望永远不会停顿 祈愿还给抽象的鸽子它的伤很重飞不起 在反光的大理石地面 我们一眨眼它就变成铸铁羽毛布满筛子 锈迹沙粒蚕食最初的构思 准确找到它的角度不容易 理想被错视时翅膀与身体分离 一张沉重的网如何游出 相似的鱼鱼雷也可能转化炮弹尾巴我们怎么办 乔奥玛.布兰萨让我们看他的疑问 一只生锈的手在抗议它从翻滚的泥土里举起 爆炸问题如果你还听不见 小指就消失指缝就会长出蹼来帝国之上的三朵云 最高的一朵仍没高过皇帝左耳 眼睛被什么遮住了良心的影子 在哪里?不少人绝望了 更多人穿越几个世纪最后被良心发现了—— 在学校的操场旁或居民区 像单杠的金属架一样实在沉稳挺拔 扎进大地并且离我们很近 沉默和寂静原本只有两页书也是两扇漆黑的门板 比人本身高大吱呀一声 你刚才开门的声音落在了这里 我没来得及说出的话也落在了这里你该明白了 寂静的颜色比沉默多一些亮度而且会越看越亮 甚至可以抓住世界的形状苦恼和颜色 很多看不清的变得羞怯 午夜的清晰灯似乎又亮了一下 如此简单现实只有两页仅仅两页就可以翻开我们 首先练习沉默!面对程序 之间的关系一个枢纽一个变小的 旋转楼梯一种转折或递进 寂静被视觉压住的部分回来了 小型的雨落在金水路上嘭嘭敲打我们回来的车篷 一种游戏 深夜恐龙在几秒钟长大 开始顶撞实验室它们的长脖子全都探出窗户 寻找出路石柱的脚超出立交桥的脖子越扬越高 它一奔跑就破坏城市翻过身子 警察的呼喊帮助了科技我们唯一的家 在哪大街广场路口蹲在梧桐树叉上 嗓子嗓子我们的嗓子在哪灯光的西番莲被压住 逃跑与摇晃一座空城 到处倒下的烟裸露的钢筋扎烂虚假的扎烂 直升机似乎有绳子悠荡绝望与峭壁 垂下阳台又悬起不幸的我们万幸坐上了假飞机 盘旋铁去洪水的范围打苦工 颠簸的一块石头对准他也对准你 可怕的距离被一种可怕的速度分解 城市要毁灭命运要撞击那就闭上眼睛吧 你与你过不去的一秒还是有偏离 一根头发的偏离一条可能性大道 擦过前额那些人为的水泥 在我们身后倒下再倒下这时你才看清烟雾 在楼角那个可怜的小勇士 拐角也不能留住他的半截呼吸他已来不及倒下 牙齿排列的黑洞吞没了一切 汽笛划伤我们柔软的心在深渊的设计中 继续下沉不过还是应该谢谢你这口头误导者—— 一个乱世英雄在普遍的慌乱中划一条出路 让我们拿走拆开的翅膀倒退一直退到游戏的入口和出口 踏上白花花的阳光真好它比一个县城的大地还坚实 月亮曾经在哪些水里捞过刀鱼 ——回乡偶书之一 一个从来不喝酒的人终于喝了 大口大口白兰地天空就要塌下来 墙豁子挤过干燥的风开花的新树枝在空中忙活着 交换旧树枝它要确定 瓦垄上的月亮是不是 月亮它曾经在哪些水里捞过刀鱼而轻铅笔 又是哪一年摘掉的帽子橡皮要是樱桃花能开出来 一辆东方红拖拉机那么信封的老住宅 就可以转动门轴 风化石的夹缝 蝎子就会找回跳双人舞的火钳 小人书与红孩子 对立黑孩子 当我的蜡线收回一叠好云彩母亲的母亲 会端上晚饭盆胳膊弯刚刚放下 浆洗白被单 一股熟悉的好味不须说出 可是我没怎么在意当然我更没在意一窝刚出生的耗子 想多嚼一点烧焦的炉火铲以便治疗牙周炎 然后在老盐罐中营造棉花糖的新生活当然这纯脆属于偶然现象 很多夏天都是如此变黏的黑土生长出一种不良倾向 杂木棵与鸟叫同时站起来有意与上学之前的小脚丫过不去 野游不知道旅游旧衣服刮坏了太多铁蒺藜 黑布鞋听不进我的话 硬要跟踪水蛤蟆呱嗒呱嗒上下午让我加倍想起我的家 那两条变凉的炉钎子让我的天空 一打闪就想起炉钩子失败的滑雪 用难以靠近的云去温暖减法 去睡眠加法灯泡啊灯泡闪光完全等于零 黄昏的斜对门站着梳头的小哑巴她转身了我(仿佛要飘出亚洲) 一排糖槭树必然因为自身的陷入而脱离 一连串不成熟的春天曾立下过誓言用早晨的光砍去斜歪的血管 腊梅 饰容春态少 万卉一枝孤 ——(清)朱枫 大地主的家是个太传统的家 有名的豪宅藏在树林中 门前石狮子想吞小溪边的冰 共迎一天小雪红对联 还没来及对出来小径似有人扫过 太阳很高了姐妹们也不下楼 更不可以出门两个怕羞的人 叽喳喳象喜鹊在枝头蹬着枯叶 细枝跟着跳与一溜头发正合拍 伸长的手指挑起画眉的眼眉 窗户上的霜毕竟太厚了朝外 反着看满院子大清早的白毛 从里到外一层纸的春天有多好 贴吧贴吧满屋弥漫浆糊香 妹妹倾向外国她说她要反传统 姐姐拽住了一大把的坏脾气 劝不了她与她生一场气 咬手使劲撕巴老半天 不论怎么说都是对联的错 累倒了才和好她们继续磨剪子 剪啊贴啊窗里窗外相当惊讶 为了春光一些脚步围绕着 积雪从外表上看不见窗户更看不见人 只有门前树皮裸露上上下下满开黄花 达菲·谢里丹(美国) 漂流 我是说从你手里刚提起的那支硬皮桨 滴落那一滴 引起的那种紧张也是紧张 一样的圆圈被另一个一样 (或更多的)推开 仿佛自己有意为自己更换一个 好地方只有在黄河中下游才会出现 被连环套套紧 侧身或其他形式的 开花浪非要在这儿开花 被反复套住的坚固的水花瓣 终究是怎么也套不住的反方向 橡皮艇边缘闪现的 总是新光环颜色膨胀 正好适合我的 赤脚当然也适合你的 出发形态让我们马上出发 住宿区的小楼蹲在身后的土坡 谁还去回顾昨夜 猫头鹰叼走萤火的花椒树 那只大扑棱蛾子 伪装裙摆两把檀香小扇面儿展开一层珍珠霜 七月的早晨没有人不是躁动的 独角仙也没有人回头去看见 白腊树下天堂伞撑开又收起 隐入颠倒的竹林 你和我的救生衣是一样的穿在泡沫马甲上 刘秀湖周围风的起因 野鸭翅膀稍微碰倒一点点弯腰的芦苇 豫西大峡谷展开全部 峡谷状伏牛山脉最后的一条大地裂 吸引今天要骑着水花穿越 贞女床以下的飞龙洞 看一系列云朵一起磨擦河南的花边 天空叠加火山口造型 小艇被石头硌了小艇跟着跳 紧接着小艇飞 女人的尖叫灌满峡谷橡皮使橡皮艇飞得更高 一团水雾罩住一团雾水 潮湿的人从上午到下午忙着潮湿 忙着开办特务的水上培训班 最新的一批彩虹保姆要在下个瞬间毕业 为社会增加合理的力量龙泉沟的流水使阳光找到了 抵触潮流的伟大形式 在浪花中找到人类最近的新起点 徐玉诺 黑蜘蛛已织满鲁山的屋檐墙角 喇叭花广播肺病的游丝 我要出去趁着冬小麦起身的火苗 拎起乡土的内力 合上背后的木头书页深呼吸 这就走到我不知道的白天去 不相信会白白地行旅直到碰见 额头上的金星 在新诗的早期谁敢把家乡铺开千里万里 撩起无边的雾试着剪裁自己的布衫 极端的南方到了 龙眼树仍是龙眼树 你已看遍繁体的油灯岁月 这是海边沉闷的夜 极端的南方不也正是 那个极端的北方吗 露珠蒸发了山路 从村口一直到溜狗的城市 银元的光晕套不住你的陶灯碗 坏人的金牙一闪而逝 当警报压低蝙蝠的翅膀 白天鹅迟疑着狂风椴树林低下了腰身 转变成土匪大兵开过黄昏 又一阵沙尘打在桂花的纸上 地板忽然下陷 一只脚的陷阱停住 这一会儿还是给老家的毛驴通个气吧 我真的很想念你们黄牛 有人要在梦里把田野揣进爷爷的蓝布袋 看吧他的眼睛注定突出蛤蟆 只有乡亲和泥土 才是真理一把桐油伞能撑起漫天的隐喻吗 无论地主新婚人性 都会在早晨找到一所婚房 门吱吱打开 镰刀蹦跳着跑向转弯的豆地 镰刀在自动割庄稼 相信孩子的正确吧哪怕小脸重叠了泥猴 与未来一起骑上那匹枣红马 响鼻在响就在窗外 同一种交响抓住太阳的缰绳即便笑声翻转了 站立的马蹄哪怕摔下来 也要向着我的土地 那么多的笑声同时铺开 遍地耀眼的好棉花 公园不过是一个临时组织强加给那片湿地的自大行为 今天可以是双休日满城人不是一般地寂寞瞧这秋天 很久很久没下雨了 雾霾也想趁机起身就像去年那样 从背后悄悄跟上 一双皮鞋搂住我们致命的腰 在城市向极端摆布的时代 迫切需要一个反转向保护区的湿地 求情而最终的靠山 却注定是一条河 的公园可自从有人硬把那里叫作公园 我的灵魂也只有硬 是反对一长条肉色石头确实立着 用红笔刻字无耻啊 渺小的眼睛怎么能看见那无限那 天上突然打开的大地 云和云迅速混合 翻滚而来一条通道 推出一部最后能镇住我们狂躁时代的电影 伟大缺口旳银幕上 一位祖先的母亲坐船而来 创世纪她用一把草叶的折扇打开 黄泥肋骨水坑继续燃烧 于是赤麻鸭飞了白琵鹭冲天追赶回声 大小天鹅都飞了只有金眶鴴留在香蒲中 注视芦苇根跩动大鸨 城里人的自驾车停在那边树荫下孩子没跑太远 一双小腿急速剪着草丛 一半的脸都在倾听刀螂收割野黄豆 荚壳爆炸蝈蝈的周围 野西瓜停止一枚鸟蛋荻花与荻花拍手 男男女女坐着草叶吃面包 一溜风的长脖子吐出一天白絮 荻花滚滚而来荻花的斧头劈开一片风水 柽柳的阴影实验一朵乳菊的香气 一人高的芦苇中有个成年人连拉带尿芦花看见了 什么都如同没看见 也有可能只看到人及其动物性(隐蔽部分) 树桩上那个内心搏斗很久的人好像在给自己反复打气 站起来回走他认定涛声拍死了一辆小汽车 能够再加上很多很多辆的尾气 颠倒诗 ——回乡偶书之二 正是这条老街我与我独行独行之后再并行 鞋帮白铁穿孔冻硬的脚轮流踩呀踩 嗷嗷的牙疼不出声眼睛想掘开路面 可能不可能翻找旧雨点积雪 太多的夹层母亲锥子 牛腿骨的漩涡拧紧红麻 斜阳飞鸟糖槭叶马车移走煤灰山我家门口对了 你家门口酸菜缸脖子扭了茶壶盖 抬高水桶姐弟俩搞试验平衡一直往前走洒了一些不要紧 坚持共产主义生活大生产溜冰垃圾坑 卷烟自行车戏匣子响铃 拔豆根割草刮大风 四小学多少红鼻尖两只手闷子打架 钻进去熊掌交叉鼻涕虫 生活委员杆秤翘尾巴女生 空土篮又交了油印粪票高兴多吃一个 发面饼起哄操场雪堆的麻雀 树梢穿透太阳课间操溜啃冻柿子小卖铺伸舌头 霍家店泥浆扒苞米学工还学农 起立点名孙克玉 笑勉强憋住窗户外飞机险些擦了瓦房脊 扭过身一排狐狸脸蛋木芙蓉 报告小报告化学反应讲台蘸水钢笔花名册 填表小业主无地自容挺住 翻过去修正反修正 从脚上的泥开始挖地道战整块砖老师说还要 举手邻居墙头缺口越多越好 跑抓不住快跑躲 起拱躬身勉强探出一个头对面刘海亮了 光洞穿土衣服泥猴回到家 母亲报怨的嘴一声长叹撇着右边 受表扬硬说香港是臭虫不摇头 不眨眼睛别墅黑暗势力 你的脸好看很不幸想想你有个地方还没洗干净 左依峰戴着羊剪绒划擦地炉子让它发高烧 关门开门看烟囱作文该交了 全体练习写景星期四的风你的很好但也有的人太空 一股烟尘起立主席像手写体天天向上 乌拉脚跺拖拉机的脚 小儿科想推走房屋长条凳一节课推开两节 接班急于长大快总是慢 十花街人群浮起铸铁 尖刺高帽子太高了父亲的头顶着头顶 流汗鼓红包地主后代跑着哭 撤职去爱风筝班长你的青春痘 挤不完伸出冻破皮的手 打算盘拉回天空麻绳捆不住北大沟 医院怪味冰我只能坐着走路腿麻痹症 春夜猫起腰演电影房梁上走过王其家 火柴给小鬼带路被星星绊倒锯末子 烤烤梨树镇黄苗子长势良好宣判没完成 树稍移动少白头混入一场大雾 打冷颤操场吴宝柱金影细腰猎狗王子中 边缘杂草铲撒白灰画圈 一圈等于四外圈里圈占便宜 两个大块头吃了哑巴亏过剩的力抬着鼓声 原地踏步抖肩膀指挥棒牵着一群小孩不在乎苍蝇 瞎子激动失眠症窗户白了猫头鹰 吹洋号喇叭筒噎住了红旗飘凉水的春风 包裹小腿仪仗队分组 男女混合接力使劲拽住空马群跑不过太平洋 不可能拍巴掌给暴风雨镶金边接力棒 手交换手往上翘你怎么掉了 铅球落泪珠的坑揉眼睛 他好像从来没吃过早饭转身卡腰小个子 总也不服气硬撑竹竿高度别提了 体育教师调教坏学生时而颠倒好学生学习应对慢性病 肯定与否定的落后之歌 在豫西偏僻的乡间仰韶最贫困的角落 陶片保留着人类原始的体温 青桐呢青桐全都埋进深夜 只有狗保持留对月亮的狂热 古典嗓门填不满古老的歌 而铁柱的院里小手扶也只呈现落后的轮廓 闷湿的夜萤虫的团伙在溪边疯狂淘洗拼凑碎金 有人出来带着反感 钟点与门外的钟点会合一串哈欠呵退一排大树 光柱自动打扫黑暗的落叶放大一汪水坑 举起铜锣的传统还是让村庄的心回到原点吧 温柔地打它给温柔涂一层奢侈的薄膜 金黄的海涌过打盹的屋檐 一床麻花被裹紧老人小孩子的梦又翻个热身 什么样的家园才是共同的公路阴暗了 一条午夜银河 穿过百人的村庄或更远 远山淡漠得要飞起来 那时偶然路过一辆摩托留下一溜偶然的油味 其实风根本不会抢走什么只是轻度分开 稠密的树叶然后继续摇动满怀新枝 一整年的劳动灌满季节 干草垛显然没有看见狸猫走眼的火星 狐狸皮难以隐瞒芦花鸡一对搭档总在疑问上走 举高手中的月亮温柔地打它 回声与回声融合给温柔再涂一百层奢侈也不会嫌多 肯定与否定的一支落后的歌但群山不会落后 爱从来也不需报酬脚步趟过年月的周期 去欢迎一天天从那边射来柿树缝隙的光 看一眼倾斜的炊烟你愿意说它有多美它就有多美 邓万鹏,著有诗集散文集《时光插图》《走向黄河》等多种,其主要作品被收入《新中国50年诗选》《——中国诗典》《年中国诗歌年鉴》《年中国诗歌年鉴》《年中国诗歌年鉴》《诗刊60年诗选》《星星50年诗选》,《绿风年诗选》等各类年选近百种。曾获首届杜甫诗歌奖、《莽原》年度诗歌奖、大河诗歌奖、河南诗人现代诗歌奖等。 诗麦芒里有麦子的味道 编辑:量山 长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a.com/mfrzp/7701.html
- 上一篇文章: 12首诗12幅书法12种花,养眼养心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