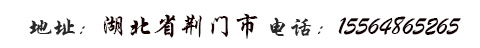今日秋分丁立梅秋天的植物
|
草香 秋天里,总能逢到修剪草坪的。剪草机“呜呜呜”开过去,草的“长头发”,一堆堆被割下,空气中弥漫着草香,是种混合着成熟谷物之香的香。浓浓的,厚厚的,取了它,搅拌搅拌,似乎就可烙葱花饼吃。 好闻,真好闻。我每遇见,总贪恋地待上一待,猛吸鼻子,真好闻啊! 今日恰逢遇见。我站在那块修剪好了的草坪跟前,看它如新剪了头发的小孩,变得又整洁又光亮。那堆积在地上的草的“头发”,可真香哪,如果用它做个枕头,一定很好。我正这么想着,修剪草坪的人过来,他冲我笑一笑,我还他一个笑。 我们的笑,软软的,也散发着草香。 下班回家,路过一片草地,小草新割了,散发出浓郁的草香。我有种冲动,想躺到那草地上去,在那草香里打上几个滚。 怎么形容这香呢?还真说不好。它不似花香,染了脂粉味。它又不似露珠雨水,带着清凉。对,它似乎有种成熟了的谷物的味道,是小麦,或是大豆。再闻,却又不是,它香得那么独特,日月雨露的精华,全在里头。你不由得张大嘴,大口大口地猛吸,五脏六腑都被它灌得醉醉的,如饮佳酿。你猛然醒悟过来,它就是草香哪,用什么也比拟不了。就像一个独特的人,你怎么看,他都与旁人不一样。他有他特有的气质,别人模仿不来。 这是秋天的草。牛或羊,一整个冬天,都吃着这样的草。牛和羊的身上,都是草香。 扁豆花说不清是从哪天起,我回家,都要从一架扁豆花下过。 扁豆栽在一户人家的院墙边。它们缠缠绕绕地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顺了院墙,爬。顺了院墙边的树,爬。顺了树枝,爬。又爬上半空中的电线上去了。电线连着路南和路北的人家,一条人行甬道的上空,就这样被扁豆们,很是诗意地搭了一个绿棚子,上有花朵,一小撮一小撮地开着。 秋渐深,别的花且开且落,扁豆花却且落且开。紫色的小花瓣,像蝶翅。无数的蝶翅,在秋风里飞舞蹁跹,欢天喜地。 人家的扁豆花,这个时候开得最好了。我上班的路上,有户人家,在屋旁长了扁豆。那蓬扁豆很有能耐地,顺着墙根,爬上墙,爬上屋顶,最后,竟一占天下。屋顶上的青瓦看不见了,全被它的枝叶藤蔓覆盖得严严实实。紫色的小花,一串一串,糖葫芦似的,在屋顶上笑得甜蜜。小屋成了扁豆花的小屋。我路过,忍不住看上一眼。走远了,再掉过头去,补上一眼。那会儿,我总要惊奇于一粒种子的神奇,它当初,不过是一粒小小的种子。 栾树 又见栾树开花了,很意外。这个时候,它们该结果才对,且有不少的栾树,已扛着胜利的果实了,红彤彤一片,如撑起无数的红灯笼。我仔细察看,开花的树的确是栾树,枝头托举着一捧捧金黄嫩粉,像一群着黄衣裙的女孩子,在那儿登高望远,金光闪闪。 太耀眼了!耀眼得我得查根问底一下。这一查,恶补了一个知识,栾树原也是个大家族,有品种好些个的。我最初见到的,是全缘叶栾树,也叫“黄山栾树”。而这会儿正开花的栾树,是秋花栾树。 栾树一边开花,一边结果。开花是热烈的,结果也是热烈的。花是黄灿灿一片黄,果是红彤彤一片红。每回见着,我都要被它的气势给震住。太浩荡了!对,就是浩荡,一出手就是一片大好河山。我站在我的楼上望过去,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它,高低起伏,绿底子上,是大桶的颜料泼洒,红红黄黄,如峰如峦,如沟如壑。 栾树的果继续红着。我去一家小超市买盐,出门,被门口一树一树的红,差点惊了个趔趄。它简直红得有些吓人,一颗一颗,心一样的,抱成一团,燃烧起来,从树上,一直燃烧到地上。满地落红!却不让人感伤,只觉得美,美到极致!去日无多,它似乎紧着这最后时光,疯狂一把。它当懂得,华丽丽转身,远好过颓败萧索,更让人记挂和念想。 我在桥上停下来,望望水。岸边有花,再力花和美人蕉。与水很配。若再配上木芙蓉,会更好看。几朵凌霄花,缠在桥栏上。有花开着,总叫人高兴。 人少的地方,我看树木。路边的树木到了最好看的时候。尤其是栾树,一边开花,一边结果。细碎的黄花,一撮一撮的,黄灿灿,高踞在树上,光彩照人。而它的果,灿如红灯笼,一盏一盏,在树上悬着。似乎是某个大户人家要办喜事了,门前廊下,全挂上红灯笼了,一派的喜气洋洋。 栾树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灯笼树”。很形象。 曼珠沙华 小时,我不识此花,它长在我家屋檐下,裸露着瘦瘦的筋骨,片叶不着。 秋雨滴答,水滴花开,一瓣瓣细长的花瓣,蜷着,像谁顶着一头的红卷发,又像煮熟的小龙虾,血红的,红得有些诡异。我回回见,回回都要被它惊住。 祖母叫它“龙爪花”。我想不明白,它与龙有什么关联呢?也只把好奇装在肚子里,看见它,也只远远看着。我们掐桃花,掐大丽花,掐菊花,掐一切看得见的花,却从未曾掐下它来玩。——小孩子是顶懂敬畏的,太美的事物里,藏着神圣,亵渎不得。 民间又一说,叫它“蛇花”。 那年,在无锡。惠山上闲闲地走,满山都开着这样的花。石头旁,小径边,或是一堆杂草中。它是当野花开着的,没有一点点优越。然独特的气质,即便山野,也遮掩不了。那朵朵的艳红,把一座山,映得绚丽夺目。我掐一枝,拿手上拍照。 旁边走过三五个妇人,她们看见我,不走了,停下来对着我,叽叽咕咕说着什么,神情甚是着急。我听不懂,只能猜,以为她们在指责我乱掐花草。我很是羞愧,手上握着那朵花,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又想狡辩,啊,它是从岩石下面开出来的一朵,是杂草堆里的,是野花儿。 一中年男人走过,看到我们大眼瞪小眼的样,赶紧帮着翻译,告诉我,这些阿姨说,你手上的蛇花是有毒的,赶紧扔了吧。 我吃一惊,赶紧扔了花。 回家查资料,果然。中医典籍上叫它“石蒜”,如此记载:红花石蒜鳞茎性温,味辛、苦,有毒,入药有催吐、祛痰、消肿、止痛、解毒之效。但如误食,可能会导致中毒,轻者呕吐、腹泻,重者可能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麻痹,有生命危险。 这让我想起“红颜祸水”之说。君王亡国,也怨了红颜。可是,有谁想过,祸水原不在红颜,而是绊惹她的那些人啊。如这蔓珠沙华,它在它的世界里妖娆,关卿何事?你偏要惹它,只能中了它的盅。——它就是这样的轻侮不得。这骨子里的凛冽,倒让我敬佩了。 木芙蓉 秋渐深,别的花草摇落,木芙蓉却层出不穷地开起花来,在满目萧索之中,捧出朵朵明艳。一朵一朵的红,像用上等的绢纸叠出来的,簪在枝叶间,你打老远就能望得见。夺目,太夺目了!叫人无端地高兴。 等走近了看,它纤细的枝条上,累累地鼓着的,竟都是花苞苞,家族繁盛、人丁兴旺的样子,你实在不知它后面还会冒出多少的花苞苞来。一个花苞苞就是一朵惊喜呀。你想到小时候看魔术表演,那个嘴里会喷火的中年男人,突然从怀里往外掏东西,他掏出一把的红绸子、一把的绿绸子。在大家的惊呼声中,他抖一抖手,再掏,又是一把的红绸子、一把的绿绸子。他掏啊掏啊,越掏越快,红绸子绿绸子便泉水样的,不断地冒出来,似乎怎么扯也扯不尽。 它就是花中的魔术师啊! 木芙蓉的花开得好,粉腮粉唇,像抹了胭脂。 写木芙蓉的诗词不少,数王维写的顶有人生况味: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闭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山中幽深,花与人家俱寂静。 它是秋天的大美人。真正的美人。回眸一笑百媚生。它没回眸,倒是惹得我频频回眸了。一大群“美人”,荡起粉红的裙摆。我几乎没办法从它们身边走开。 枫树 枫树红了,是从顶部的叶,率先红起来的。我站它旁边,看它的叶子怎样被染红。我觉得不可思议。明明几天前,我见着它还是一树青绿的。谁给它染上色的呢?是风吗?是雨吗?还是夜露?还是闲得发慌的鸟? 鸟只管唱歌。 一老者坐在枫树下的一条长凳上,他在听京剧。他微闭着眼,一边跟着哼,一边打着拍子。一树枫叶映着他的人。他许是见着枫叶红了,许是没见着。我走很远,回头,觉得那一人一树,是再搭不过的美好景致。 有一棵枫树,很高了。扛着一头一肩的红,红是不得了的红,红到红里头去了的红。树下,歇着一个青年,他背倚着树,在发呆。青年知道他正倚着一树的华美吗?真想他抬头看看,再看看。这样的时光,怎么度过都叫人心疼和不舍。 杉树 我缓缓走在一片杉树林里。我成了一棵会行走的杉树。我和时光,都慢下来了。 有好一会儿,听不到声响,一点儿也听不到。没有鸟叫,没有虫鸣。它们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吧。这是十月,风,还有太阳,还有夜晚的露珠、星星和月亮,或许还有飞鸟,还有虫子,它们你一笔我一画的,在这些杉树的身上,描上了秋的影子。不算深,亦不算浅,是恰到好处的斑斓。 天光敞亮、透明。白日光幻化成无数条调皮的小鱼儿,在那些枝叶间,在林中空地上,在空地上的那些野花野草身上,蹦蹦跳跳。它们银色的影子,划过我的发,我的眉,我的肩,我的衣袖。待我想捉住它们时,它们又从我的脚跟边溜走。 突然,风起。哗哗哗,哗哗哗,所有的杉树叶,一齐欢唱起来。整个杉树林顿时山呼海啸,万马奔腾。看上去那么柔软的叶子,力量竟如此巨大! 随便一处,都可以坐下来,地上不脏的。铺着落叶的地毯,哪里会脏?我倚着一棵树,顺势坐下来,闭起眼,听树们说话。风轻时,它们的说话声也轻,有些窃窃私语的意思。像谁的手指,滑过琵琶,轻轻弹拨着。风大时,它们欢腾起来,竹板敲起来,胡琴拉起来,还有葫芦笙,还有架子鼓,还有萨克斯。好了,一首它们自编自导的交响乐,就这么热热闹闹地上演了。惊涛骇浪,仍又不失华丽浪漫。 它们这是为谁演奏呢?为我吗?我听着听着,独自笑了。 “层林渐染”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这个时候的杉树的吧?那细如缝衣针似的叶子,一点一点描上红,描上黄,是怎样的浩荡激越!它叫我无法呼吸,真的无法呼吸了。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声音说的都是,感谢上天,让我拥有明亮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些。 梧桐 秋天的斑斓里,梧桐是立了大功的。 它在每一片叶子上,描着秋色,或褚红,或焦黄,或褐色。满树撑着,像立体的油画,悬在树上。 孩子们在树下捡梧桐叶。一孩子说,它像手掌。一孩子说,它像蝴蝶。一孩子说,它像扇子。一孩子说,它像小舟。孩子们的想象力很神奇,他们的世界,就是一个诗意的王国。我特喜欢“像小舟”的这个比喻,秋天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叶小舟,它们扯起风帆,就要乘风远航了。 每一片梧桐叶,都像是帆,鼓胀着秋色,就要远航去了。我在一个学校讲座,完了,一孩子气喘吁吁跑来,手里拿着一片刚捡到的梧桐叶,褐色焦黄的,看去,很像一张牛皮纸。孩子请我在上面签名。我高兴地一边签,一边问那孩子,为什么想到捡片梧桐叶来给我签名呢?孩子答,我觉得它很美。我抬头看那孩子,红扑扑一张脸,有着鼓鼓的额,像只饱满的橘。 桂花 这几天,走路一不小心,就会被一个小家伙偷袭。 它偷袭你,不分场合,不分心情,不分雨天还是晴天,不分白天还是夜晚。反正只要它高兴了,它就会偷袭你。 而被偷袭的你,绝不会埋怨,绝不会厌倦,倒是要一脸讨好,欢喜心雀跃,深深吸一口气,再吸一口气,呀呀,小家伙,是你呀。 对对,它的名字,叫“桂”。 我在这时,总要追着去捉它。有时,是在一片林木后。有时,是在一户庭院里。有时,就在道旁,它站在那里静静的,笑嘻嘻等你,不藏不躲了。 花朵貌不惊人,还是那么小,米粒儿般的。跟从前一样的小。跟远古时期一样的小。 远古远到什么时候呢?那会儿,它住在深山老林里,和荆棘、葛、荨麻、野葡萄是邻居。 是谁先发现它的小身体里藏着的那一粒粒香的?我甚至能想象得到那一声惊叹的“啊”,是如何惊动了一座林子的。 啊,真香哪! 风比虫子发现得要早。虫子又比人发现得要早。 到汉代,终有人把它引种到庭院。从此,它让烟火都染上香了,它让诗词都染上香了。 “绿玉枝头一粟黄,碧纱帐里梦魂香”,想想,世上有这样的好花好香,年年秋天都来骚扰你,也是人生幸事一桩呢。 桂花开花,一点儿不矜持,是非得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不可。蕊黄,花朵细碎,如米粉。虽其貌不扬,可人家香哪,香得那么理直气壮底气十足,它偷袭于你,叫你如何把持得住!它是粘人的小妖精,却不讨你嫌,你就那么甘愿被它俘虏,被它的香绊住脚步绊住心。你想吃桂花汤圆了。你想吃桂花羹了。桂花莲藕也正当时。如果再喝一点桂花酒,佐以桂花米糕,那日子真是太惬意不过了。 我喜欢这样地遇见它。还隔着老远的一段距离呢,它就满身喷香地跑过来了,用香吻我。我一惊一乍,呀,桂花开了呀!却不知它藏在哪里。或许在一个幽深的庭院里。或许就在路边的那些杂树丛中。 寻找它也是桩顶有情趣的事。到处去寻,穿小径,拨草丛,有时还要扒着人家的院门,往里瞅。它点着迷魂香,让你晕乎乎的。你闻着香去,以为它一定在这处,却扑了个空。它的香又跑到那里去了。最后,终给找到,那惊喜就像捉住一个擅躲迷藏的高手,你就差得意高喊,我捉住你了! 闻够它的香,还不行,必得摘上一小把,在口袋里装装好。一路走,一路触摸着,心里真是欢喜,这人生真是十分的好啊! 到家,那手指都是香的,不舍得洗,不时举着,闻闻,独自快乐小半天。 夜色拌调,再蘸上夜风几缕,虫鸣几声,秋露几滴,外面的香,便越发地浓情蜜意起来。勾人魂。 这是秋天精心烹饪的一道大餐,“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为伊忙”,偌大一个天地,都在喷着香、吐着甜,像刚出炉的蜂蜜糕。 对了,是桂花开了。 一出楼道口,花香就兜头兜脸地扑过来。我明明是有准备着的,还是觉得被它偷袭了,脚步欢喜得一个趔趄,哎,多好多好啊,是桂花哎。 小区里也不过植着三两棵桂花树,就香得无孔不入前赴后继的了。晚上,在小区里散步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人影绰绰。他们在花香铺满的小径上,来来回回地走,语声喁喁,搅动得花香,一波一波地流淌。我想,他们定也和我一样,闻着香的,有些贪恋。 草地上的几棵桂花树,也开始播着香了。别看这花模样细小,文静着、害羞着,甚至有些怯弱,像未曾见过世面的小女子,一颦一笑里,都藏着小心。事实上,才不是呢,它的性子猛烈得很,能量也大得惊人,是那种随时随地都能捋起袖子,豪气得敢跟男人拼酒的角色。它一旦香起来,那是想收也收不住的,气势磅礴得很有些撒泼的意思了。却撒泼得不惹人厌烦,反倒叫人满心欢喜,宠着、爱着,不知拿它怎么办才好。一棵树,十里香。谁能拒绝它的甜与香呢?再多一些,再再多一些,也不嫌多的啊。是恨不得和它一起撒泼,和它一起醉过去。 桂花香得很剽悍。 只要出门,就能闻见。庭院里,河边,树丛中,它势力庞大,无处不在。 不出门也能闻见。它跑在风的前头,穿庭入户,喧宾夺主,不拿自己当外人。 我们也不拿它当外人,任由着它屋内屋外乱窜。 能说什么呢!这天,是它的天。这地,是它的地。它霸道得独一无二,却不遭人嫌,闻见它的香,人都要喜出望外一声,啊呀,桂花开了呀。 当然。 它全副武装披挂上阵,所经之处,无一不对它臣服。 它是花里的穆桂英。 它的香气,乘风扶摇直上,抵达我的七楼。我在阳台上,闻见它的香。我走到客厅,闻见它的香。走到书房,闻见它的香。我去厨房,倒一杯水喝,水里面也浸着它的香。我看书,书上歇着它的香。我写字,手底下迸着它的香。衣服上随便抖抖,就能抖落一堆的桂花香。 银杏 市民广场上,长一排银杏,又一排银杏。片片叶子,都像用金子镶上去的。镶上去也便罢了,偏偏还精雕细琢了一番,镂岀好看的花纹,每一片,都如一只金色的开屏的小孔雀。一树的“金孔雀”,在阳光下,怎一个富丽堂皇可比得!却又不显得庸俗,而是极其高雅端丽的,又捎带着活泼,我喊它们,“迷人的小妖精”。 银杏的叶,偏偏像花朵。一树的叶,远观去,不得了了,像开了一树金黄的花,把半角天空,都染得金黄。它是历经大富大贵的女子,活到七老八十了,还端着骨子里的优雅。——纵使转身,亦是华丽的。仲秋的天,因它,平增一分明艳。 它又是个伟大的乐师。每一片金黄的叶子里,都藏着音符。风的手指轻轻一弹,便响彻四野。当然,你若不专心聆听,是听不到的。自然的秘密,都是藏而不露的。 银杏绝对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它一旦秋起来,那通身的富贵气,绝对耀眼璀璨,你假装看不见也不行。它就是那么雍容那么不可一世,你还能怎么样呢?你只能惊叹。我在一个从前的私家园林里,看到一地的银杏叶,铺成黄金毯。我站着看,只觉得好,好得不能再好。那个光阴,那个遇见,对我,如同馈赠。 看管园林的老人说:“这叶子,我们不扫,留着看呢。”我不由得多看了老人两眼,老人瘦瘦小小的,两颊凹陷,唇旁有个蚕豆大的紫斑。这样的老人,在大街上的人群中走着,大约是没人愿意留意的。可他在一地的秋色旁站着,就有了明艳和亲切,浑身散发出满满的好意。“留着看呢。”他说。这话让我激动,多好!把秋色就这样挽留着,能留多久,就留多久。 菊花 从前的乡下,人家的房前,或篱笆墙边,都植有几丛,或金黄灿烂,或红粉乱扑。秋来,它们且笑且开,静谧的时光里,浸泡着它们的颜色和香气。女孩子们天天有花可戴。戴一朵黄菊花,戴一朵红菊花。或者,今天戴朵黄的,明天就掐一朵红的来戴。 它们总要开到第一场冬雪降临。最后一抹黄,和红,会从冬雪下面探出头来,跟这个世界温柔地告别。我们路过它,疑心下面藏着一条黄帕子和红帕子。 一场秋雨,再紧着几场秋风,菊开了。 菊在篱笆外开,这是最大众最经典的一种开法。历来入得诗的菊,都是以这般姿势开着的。一大丛一大丛的,倚着篱笆,是篱笆家养的女儿,娇俏的,又是淡定的。有过日子的逍遥。晋代陶渊明随口吟出那句“采菊东篱下”,几乎成了菊的名片。以至后来的人们,一看到篱笆,就想到菊。唐朝元稹有诗云:“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秋水黄昏,有菊有篱笆,他触景生情地怀念起陶翁来。陶渊明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能被人千秋万代地记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家篱笆外的那一丛菊。菊不朽,他不朽。 我所熟悉的菊,却不在篱笆外,它在河畔、沟边、田埂旁。它有个算不得名字的名字:野菊花。像过去人家小脚的妻,没名没姓,只跟着丈夫,被人称作“吴氏”“张氏”。天地洞开,广阔无边,野菊花们开得随意又随性。小朵的,清秀,不施粉黛。却色彩缤纷,红的黄的,白的紫的,万众一心齐心合力地盛开着。仿佛一群闹嚷嚷的小丫头,挤着挨着在看稀奇,小脸张开,兴奋着,欣喜着。对世界,是初相见的懵懂和憧憬。 我走过一小块草地,草地的边上,有建筑正一幢连一幢地拔地而起。秋不管的,它兀自让小野菊们,黄一朵白一朵的,插满了草地。清晨的空气,薄凉得恰到好处,露珠在每一朵小野菊上停留、闪亮。我止住脚步,怔怔看那些小野菊,猜想着它们是从哪里迁徙而来。又或者,这里本来就是它们的家园,只是被贪婪的我们,一日一日给侵占了。 我不知道它们在这里,还能待多久。但我知道,只要存在一天,它们就不会放弃盛开。我看见它们,就像看见故交。也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只在心里默默地招呼一声: 嗨,你也在这里,真好啊。 狗尾巴草 狗尾巴草站在路旁傻笑,秋天给它穿上了金缕衣,珠光宝气的。它很不习惯这身新装,觉得别扭,它还是喜欢它的土布衣衫。它不好意思地说:“哎,哎,这像什么呀,这不是我嘛。”它笑得直打战,缀满头上的那些“金粒子”——它的籽,就再也撑不住了,“噗”的一声,掉下几粒来。再“噗”的一声,掉下几粒来。 来年春天,它的脚下必是一地繁茂。想想吧,谁有它足迹宽广儿孙满堂?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能见到它。它在屋角下的一只破瓦盆里。它在人家屋顶上的瓦楞间。它在高高的纳木错湖畔。它在巍峨的泰山脚下。这世上,没有它到不了的地方。古人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里面,断断少不了它。 选自丁立梅作品《写作原来好有趣:美丽的四季·秋卷》作家出版社出版 相关阅读《写作原来好有趣:美丽的四季》 是丁立梅专为学生打造的写作课堂,此为夏卷 “美文赏读”“同步诗词”“同步生字” “同步词语”“文字游戏”“涂涂画画” 丁立梅老师手把手指导 独家首次发布丁立梅老师诗歌四首 收录四季小常识 轻松好玩,快速提高阅读写作水平 购买链接: 在这本书里,遇见高清彩色的鲁迅 鲁迅是暖男?鲁迅是宅男?鲁迅为什么不喜欢猫?鲁迅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小嗜好?…… 王蒙:读书需趁早 作家出版社7-8月新书推荐 不上课外班,家长应该如何鸡娃? 作家出版社6月推荐书单 阿来:“作家不要陷入对奖项和版税的幻想” 贾平凹:低层次的人,总爱做这三件事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a.com/mfrtz/9018.html
- 上一篇文章: 苍溪诗联格律诗词十三苍溪诗联20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