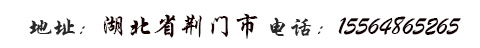梦溪我的似水流年middot溪口
|
我梦里见过的小学,常常包围在一片金黄的林荫中,阳光透过一棵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梢,投下星星点点的光晕。一阵轻风吹过,片片黄叶飞落而下,铺满斑驳的水泥操场。我还常常在梦里看见校门口的木芙蓉树,芙蓉花开的季节,风中摇曳着一树粉红。还有食堂门口轻舞柔条的柳树,蓝球场边郁郁葱葱的夹竹桃,晚自习时随着夜风不时飘进教室的夜来香…… 从年到年,我和同伴们一起在老村的溪口小学上满了七年(含幼儿园)。那是村里 的一所学校,含幼儿园加六个年级,一个年级两班,每班有四十多名学生,无论规模还是师资条件,都仅次于当时镇上的中心小学。 我升入初中的第二年,小学便随着举镇的库区拆迁率先搬到了新村的面头山,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从这个意义说,我们是老校区的 一届毕业生,虽然在后续的很长时间里,我不只一次地路过和进去过新村的小学——近三十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昔日的新校舍时至今日也早已老态龙钟。但在我的记忆中,溪口小学的老校依然只有一座,在昔时的老村里,在今日的烟波下,在我们的记忆中。 学校不大,却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教学楼是双层的一排木板房,呈折尺形排列,1-3年级在楼下,4-6年级在楼上,拐角处刚好作教职工办公室。或许因为年代久远,木地板开裂了不少,踩在上面,嘎吱作响,一不小心还会把脚尖或脚跟陷进去。下课或放学,走廊上人来人往,便会荡起许多烟尘,在阳光下像无数快活的小精灵,上下翻飞。 教学楼环绕着水泥操场,小的也仅够全校学生课间勉强摆开队列做第6套广播体操。因为空间有限,做早操的时候,有的班级便不得不挨着操场周边的法国梧桐树,错落排开。 早些年,学校还没有正规的周一升旗仪式,后来大概上面有要求,便在操场前端中央靠近办公楼位置,用水泥垒起个一米多高的旗坛。正对旗坛的二楼走廊也安装上麦克风。每逢集训,表现 的高年级学生,胳膊上别着大队长的三道红杠,站在旗坛上代表全校师生整队和升旗。之后,校长或教导主任便会站在二楼的走廊上,对着红布缠绕着的麦克风话筒,中气十中地演讲或训话,气流透过高音喇叭,在操场上空久久回荡。 然而多数时间,台下的我们心不在焉,位置便利的更将身影缩在班主任老师们目光看不见的树梢后,看树根下面的蚂蚁搬家、蜗牛上树,或者用指甲在裸露的鱼肚白的树皮上漫无目的地鬼画符着……只等一声解散的口哨,于是轰隆隆成鸟兽散。 教学楼背面还有一个简陋的土操场,因为安有蓝球架,我们日常都叫蓝球场。虽是最原始的黄土地,却不妨碍我们在阳光下挥汗如雨。尘土飞扬间,中间的黄土地早被踩的硬实平整,但球架的两头依然杂草丛生,野花盛开,春天的时节吸引来蜜蜂和蝴蝶在上面飞舞流连。 或许那时真是阳光太足,万物生长总是过于繁茂,以至每年暑假之后,高年级同学总要带着锄头来这里进行 次大扫除,但无论怎么锄,到了来年必定又是春风吹又生。 而位于两块操场间的教学楼,主体的教室环境也很简陋,前后黑板,左右两面简易粉刷的白墙上,嵌着几扇玻璃窗户,中间便是两人合坐的四组课桌椅。椅子是木头的长条凳,桌子是木头的长条桌,年深日久,桌面疙疙瘩瘩,还有不少“刀耕火种”的痕迹,祖师爷大概就是那位在三味书屋里刻下“早”字的豫才先生吧。 但那时,男女同桌的我们倒不喜欢刻“早”字,最喜欢的是在二分之一的中间画上条 。无论桌子换了多少主人,这条中间的刻痕总是越来越深——在我们懵懂而不知感情为何物的小学时代里,总爱把异性的同桌视为阶级敌人,理所当然、旗帜鲜明地捍卫着自己的领地;而等到我们升上初中,开始逐渐进入异性相吸的年纪、渴望“借半块橡皮”的旖旎时,老师却再也不给我们创造男女同桌的机会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 的悲哀。 小学期间,我和廖克群分在(1)班,杨建银分在(2)班,中间就隔着一层单薄的板壁。所以多数时间,我们仍然形影不离,形成相对固定的圈子,这个圈子后来随着新朋友的加入、老朋友的疏远而不断调整,到小学毕业的时候,俨然也有近十人左右的规模。 廖克群以超出同龄人的牛高马大,毫无疑问成为我们中的灵魂人物,他也是我小学时代里相伴时间最长的同桌。 最初老师同意我们坐在一起,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可以取长补短。后来把我们调开,则因为我们个子差距实在太大,高低起伏,比例失衡。 廖克群四肢发达,身体素质极好,据说他父亲从小就跟着拳师“摊拳头”(即练拳),不知是不是受此影响,从小他就喜武厌文。他家后院的梁下一直吊着一个沙包袋,空的时候,常常见他不知疲惫地在那里挥汗如雨。 而一到写字背书,他就明显耐心不足了。他在学校的表现,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很有些特立独行,甚至是桀骜不驯。例如老师要求写生字,用“田”字格写满一页,我们都用铅笔,老老实实地抄写。他却抡起粗重毛笔,字字千钧,墨透纸背,别人写9个字的空间,他1个字就占全了。可惜老师们都不认可他的这种小聪明, 往往追加不少体力劳动作为惩罚,如擦玻璃、倒垃圾、扫教室等。每回在我看来,廖克群都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可每回他都乐此不疲。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便干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疯子”。他则回敬我为“木头”,意思是我木木呆呆,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开始只是我俩互相叫着玩,后来却传开了,成为我们一生的绰号。 小学期间,我们的老师很少跟班,几乎上一两年级就换一批,但都一无例外地以教学严厉著称。学习上达不到老师要求,罚写字背书是司空见惯,罚义务劳动也是家常便饭,有时还会罚站、打手心等。 那时的教学环境比现在单纯的多,没有课外班,没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a.com/mfrtz/8105.html
- 上一篇文章: 为何个城市中却只有57种市花
- 下一篇文章: ins里风靡的自然寻宝游戏,秋天我在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