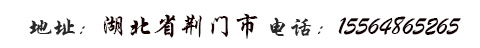名家与云南怀念汪曾祺
|
汪曾祺 怀念汪曾祺 李敦伟 当代著名的京派作家汪曾祺年出生于江苏髙邮一个大户人家,祖父是清末科举““拔贡”。父亲汪菊生(字淡如),多才多艺。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时,因肺病去世。汪家亦儒亦商亦耕,汪曾祺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熏陶。在战乱中度过童年和少年,20岁时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了西南联大中文系。他曾在《泡茶馆》散文中称自己是“昆明的文林街、北门街茶馆里泡出来的作家”。 汪曾祺的一生经历了现代中国启蒙救亡、文革运动审查、新时期改革开放等时代历程。尽管苦难挫折一直伴随,但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创造了积极乐观的诗意文学人生。他博学多识,情趣广泛,酷爱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研究颇深。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77岁去逝以后,家乡江苏髙邮为他建立了汪曾祺纪念馆、汪曾祺文学馆、汪曾祺故居供游人瞻仰。 汪老离开我们21年了,可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依然被世人传颂。其作品自然传播的影响力,直至今日,他的各种版本作品集在书店也买的很好,云南的新媒体、自媒体都在不断传扬汪老写昆明那些隽永的美文,不愧为继承了沈从文先生“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魅力的文学名家。 中国作家很多,但能称之为“永远”的非常少。“永远的汪老”是广大读者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尊敬。这得益于他在中国作家当中威望极高、人缘极好、乐于助人、善于指点,是大家心目中的“老顽童””、“老朋友”。个人经历几经波澜,潮起潮落的汪老,作品主流始终坚持积极向上。他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他对生活的信念朴实无华,认为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会好起来的。即便在人生最低谷,他也能感觉到生活的诗意,发出“生活是很好玩的”的感慨,成为他相信人可能“欢悦的活着”的根源。 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常常回忆与汪老相处的往事。写此怀念短文,追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听过他的文学讲座,参加过有他在场的作品讨论会和文学笔会,也曾陪与《滇池》和兄弟期刊的同仁去他家请教拜访。 最难忘是年末,我独自去汪老府上取稿辞行的情景。我在隆冬里,骑着自行车,从西四北穿城至南端的蒲黄榆小区,汪老的宅第。敲门后,听到屋里有拖鞋的响声,来开门的正是汪老本人。他看我满脸冻得通红,一把将我拽进屋里,帮我脱去外套,边挂衣服边说:“小李子,大冷天让你亲自来家取稿,辛苦你啦!” 我赶紧说:“汪老千万别这么说,这是我们份内的事。您老能给地方小刊物赐稿,是对《滇池》最大的支持,感激都来不及呢。” 汪老对云南情有独钟,凡云南来的客人都格外热情亲切。他让我今天多呆会儿,说晚上亲自下厨做饭做菜,为我返昆饯行。汪老的盛情如一股暖流通透我全身,坐在他不到8平方米的小书房兼卧室,心想这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怎么就住这么狭小的房子?他敏銳地看出我的疑惑,风趣地说:“我是名符其实的‘家属’,住着夫人单位分的房子。虽小,可乐在其中。” 听汪老聊天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他学识渊搏,谈吐幽默风趣如阳光般能照亮人心。说起来,汪老也只是曾经客居昆明,但他整个下午对我津津乐道的全是昆明的人和事,对昆明的熟悉程度非同一般。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所流露的对云南的那份特殊情感和眷恋,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常住昆明的人。 汪老在昆明一共呆了7年,除了在茶馆里读书写作的别样青春岁月,其中2年因生计所迫,曾在昆明北郊观音寺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故难忘记独具韵味的云南风情、花草树木、果蔬美味、以及风光民俗。但最为留恋的是恩师、同学和朋友。 汪老在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讲述了与恩师沈从文的故事。他从小就喜欢沈从文的书,阅读过多遍《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19岁告别家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但直到大二,才有机会近距离看到踏进教室门来授课的沈从文先生。见老师第一面的感觉,与平日里的想象实在不同,他瘦小的身躯,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篮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脸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汪老当时有点紧张,沉默了好几分钟,终于听到沈从文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沈先生讲课没有肢体动作,声音很低,加之有点重的地方口音很难听清楚。不少同学终因沈先生授课不易听懂,听课热情而日减。唯独汪老,沈先生讲的课是越听越有滋味。他们仿佛心有灵犀,沈先生也很欣赏这个能听懂自己课,叫汪曾祺的学生,并收为入室弟子。 说到这儿,汪老略有几分得意:“还可以说,我是先生的得意高足”。 生活里,汪老向沈先生借书还书,陪他上街逛寄卖行、旧货摊、买火腿月饼、经常听沈先生和客人谈天说地。饿了就和先生一起,到他宿舍对面的小铺子,吃一碗加鸡蛋的米线。有一回,他一个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恰巧被演讲回来的沈先生撞见。他以为是个难民,走近了才发现是汪曾祺,二话不说和两个学生把他扶到自己住处,灌了好些浓茶。还有一次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髙,沈先生看到一句话没说,跑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说让汪曾祺吃了消火。 后来汪老去了上海,因为没有找到工作,带的钱也所剩无几了,一度情绪低落,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沈先生知道后,特地写信痛骂了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还要自杀,真是没有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沈从文为了鼓励汪曾祺,还在信中说了他自己刚到北京所遇到的困难…… 汪老认为,沈先生不仅是教授自己写作的恩师,更是他人生的指路人和导师。他师从沈先生,敬重沈先生。敬重先生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就用一支笔,打出来一个天下,让自己成为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 而一代文学名家沈从文,向文艺界推荐汪曾祺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沈先生欣赏自己的学生汪曾祺,汪老也不负众望,用才情和生命,写就了那么多不朽的作品,成为当代闻名遐迩的京派作家代表人物。也谱写了沈从文先生与自己非常特别的师生情谊,一直在文坛传为佳话,也铭记在我心中。 汪老一聊云南,总是兴致很浓。记得他那天还讲了一则几十年前听来的笑话,说有一个姑娘,牙长得很好,就有人问她,姑娘多大了?她回答17。又问住哪里?翠湖西么?她答辣子鸡。过了两天,姑娘摔了一跤,磕掉了门牙,有人问她,姑娘多大了?她回答15。又问爱吃什么?她答麻婆豆腐。 说实话,我当时听了真不觉得这则笑话好笑。现在想起来才醒悟汪老是想念昆明了,想起翠湖边上熟悉的人和事,以及笑话里那位越长越小,天真烂漫的有点儿傻大姐味道的翠湖姑娘。 汪老边喝茶,边真情缓缓接着聊。他记得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雨季,翠湖的柳枝真是绿得像要滴下水来。而那时的湖水极清,夏天的夜晚,他们经常在湖堤漫步,或在堤边浅草中坐卧…… 汪老年离开昆明,他与我叹惜时间过得真快,一别已是28年。而昆明的翠湖,还是他想念的地方。所以他是中国写云南散文、诗歌最多的作家,也是最钟爱云南的作家。他对昆明的真情实感,全都通过他的神来之笔,书写成美文呈现于世人。其独具韵味的云南风度和昆明诗意,构成《汪曾祺与云南-——气质与格调》的著作,完全可以当成记载老昆明历史风貌的散文小品来阅读了。也可以说,他所有写云南的著作,都是留给云南独一无二的人文精神财富。 另外,汪老的纯真质朴和平易近人,是众人皆知的。在他家里,从夫人到儿女,孙女到外孙女都可以喊他“老头儿”。他除了奉献美文外,还是圈里公认的“美食家”,他写昆明的韭菜花、干巴菌、汽锅鸡等菜肴读者过目不忘。他不仅会品味,自己也会为家人和朋友精心烹制。 那天给我饯行,汪老特意下厨掌勺做了几道拿手菜,让我品尝。他动作麻利,不一会儿功夫,菜肴便上了桌。每上一道菜,他都能道出做法和典故,这比听他讲小说的写法还要有意思,长见识。我边品尝边说:“好吃的不见得擅长烹饪,但会做的必定好吃,汪老您真是两者倶佳了。” 我一个普通写作者,能吃到汪老这样的文豪亲自下厨做的践行晚餐,真是太不同寻常了。我曾品尝到的这顿不同凡响的家宴,是别具一格的文化,是文学圈的典故,是中国文人的情趣和精神生活,让我吃出了人生的奇妙和灿烂! 酒足饭饱,我没有忘记请汪老题词。他拿上题词本回到书房,取出碳素笔,架上眼镜,极其认真写下:“寸心藏四序,—笔画三迣,滇池八百里,归去好吟诗。送敦伟同志回滇汪曾祺八四年十二月”。 这苍劲的题词,对我有一种滋润生命的温暖,我爱惜它,把它作为信物珍藏,以寄托对汪老的深情怀念。 岁月无痕而有情,中国文坛公认的一代文学大师汪曾祺,随着他离世的时间越走越远。然而,他独具特色的干净美文,却让我们在这个“物质年代”里越来越近。今天,我们随着汪老昨天纯粹的文字,走近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走近那些真情又让人温暖的文字,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眼前…… 汪曾祺简历简介 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书画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髙邮,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熏陶。在战乱中度过童年和少年。他通过自身的努力,20岁考上了西南联大中文系。曾在昆明北郊观音寺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二年,后转入上海民办的致远中学任教两年。年春,去北京失业半年后,找到了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年3月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任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一年。年返京,先后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反右”时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 年冬调回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执笔改编同名京剧《芦荡火种》。“文革”划成“右派”关进“牛棚”。年获得“解放”。 年5月21日,因参与改编京剧《沙家滨》有贡献,而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被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作代会上理事。年2月26日在京入党,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作代会上顾问。年5月16日因病抢救无效辞世,享年77岁。 汪曾祺主要作品—— 小说《复仇》《落魄》《鸡鸭名家》《羊舍一夕》《看水》《王全》《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芳》《鸡毛》《故里杂记》《李三﹒榆树》《鱼徒》《晚饭花》《皮凤三楦房子》《钓人的孩子》《鉴赏家》《职业》《八千里》《小说三篇》《求雨﹒迷路﹒荬蚯蚓的人》《尾巴》《故里三陈陈小手﹒陈四﹒陈泥鳅》《云致秋云行状》《星期天》《昙花﹒鹤和鬼火》《金冬心》《讲用》《拟故事两篇》《螺蛳姑娘仓老鼠和老鹰借粮》《日规》《故人往事》《戴车匠﹒收字纸的老人》《如意楼和得意楼》《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幽冥钟﹒茶干》《虐猫》《八月骄阳》《安乐居》《小学校的钟声》《王四海的黄昏》《故乡人》《打鱼的金大力钓鱼的医生》等。 散文《国子监》《下水道和孩子》《果园杂记》《葡萄月令》《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跑警报》《天山行色》《湘行二记》《水母﹒葵﹒薤》《故乡的食物》《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花园》《夏天》《冬天》《人间草木》《北京人的遛鸟》《故乡的元宵》《昆明菜》《五味》《手把肉》《豆汁儿》《寻常茶话》《泡茶馆》《七载云烟》《新校舍》《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赵树理同志二三事》《闻一多先生上课》《胡同文化》《看画》《老舍先生》《观音寺》《午门忆旧》《泰山片石》《木芙蓉》等。 本文作者:李敦伟 “出生在浙江、成长在南京、 读书在重庆、当兵在云南、借调在北京。” -李敦伟自述- 年8月出生,安徽六安人。大专学历。小学至中专分别在南京、重庆、昆明就读。中专毕业参军,在部队任战士、班长,师宣传队、电影队队长、军宣队创作员。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国防战士报》《云南日报》发表过诗歌、散文、评论、话剧等,并因此出席全国青创会。 转业后,先后在《工农兵演唱》《滇池》《人民文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任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主编助理。曾是中央电視台中国电視剧制作中心编辑,影視公司总经理、制片人、中国制片委员会委员。 艺术简历 主要作品 诗朗诵作品《最后一班岗》长诗,获全军文艺奖。散文《最幸福的时刻》、评论《革命赞歌》、报告文学《代乃山战役》、话剧《指北针》等。 出版编辑 先后参与编辑出版《宏艺文库》、著名作家《王蒙文集》《蒋子龙文集》《刘心武文集》《丛维熙文集》《宗璞文集》。 策划编辑 参与策划编辑电影《长征》《花腰女儿红》《老树》等。 策划编辑 参与策划编辑电视剧《你不可征服》《太阳当顶的地方》《张学良将军》,荣获飞天奖的《小墩子》,荣获骏马奖的《火把寨的故事》。 制片人剧目 担任制片人的剧目有荣获北京优秀电視剧奖的《龙珠》,《女装甲团长》《趁我们还年轻》《待到山花烂谩时》等。 已发 1.冯牧——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2.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3.从驿路梨花到杏花如雪——读彭荆风短篇小说精选集《驿路梨花》 4.「名家与云南」睿智王安忆 5.「名家与云南」温故而知新 6.「名家与云南」格超梅以上,品在竹之间 7.「名家与云南」温润君子曹文轩 8.「名家与云南」蒋子龙在“文学新时期”的一次云南行 -全新栏目- ◇学界真传◇ ◇家族记忆◇ ◇口述历史◇ ◇社会档案◇ 栏目策划◇徐玉玲韩旭 编辑◇徐子媛韩朔 内容总监◇谢阳 视觉呈现◇益珲 一个有态度,有深度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a.com/mfrpz/8844.html
- 上一篇文章: 中国的国花是什么结果有点吃惊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