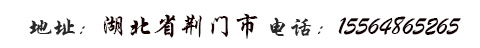御沟传叶大唐宫女的ldquo朋友圈
|
读诗说古第1篇 唐寅·红叶题诗仕女图(局部) -1-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闭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这是《全唐诗》中收录的中唐顾况(-)的《叶上题诗从苑中流出》诗。由此引出顾况与东都洛阳上阳宫宫女御沟传叶、寄情唱和的故事。事出唐僖宗乾符二年()进士孟棨著录《本事诗·情感》,说的是顾况在洛阳与诗友们游于宫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上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为之震动,遂决定“跟帖”,次日也题诗于红叶上(即本文文首所引诗),并来到御沟上游,将其漂于水波之上。十多天后,有人于苑中寻春,又得红叶题诗,便拿给顾况看。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顾况与宫女传叶发生在唐玄宗天宝(-)末年,此后唐德宗贞元(-)中年有进士贾全虚、唐宣宗大中(-)年间有到长安应举的诗人卢渥、唐僖宗(-)时有襄阳进士李茵、书生于祐等人,皆于御沟得花叶题诗、红叶题诗。与顾况不同,后面提到的这几位,以流水诗叶为媒,几经巧合转折都与宫女结成姻缘(后人有不忍顾况如此优美故事戛然而止者,添加了安史之乱中顾况宫中救美终结良缘的完美结局,小说般演说而已,不足信也)。这真是应了佛家所言:人世间的一切无非都是因为有缘而相聚。正是因了这般奇缘,红叶题诗、御沟传叶的故事千百年来为后人演绎不绝,对落叶流水寄予了无限情感。也因其传媒创意的新颖、浪漫,成为宋代“话本”小说、元明杂剧的热门题材,文人墨客也津津乐道。清代戏曲家李渔更是藉“御沟题红,千古佳事”,特制一秋叶状匾额,称“秋叶匾”。新中国成立后的年,根据田汉润色的剧本拍摄的琼剧古装电影《红叶题诗》,一经上映,好评如潮。顾况画像 红叶题诗之流传可谓滥觞,个中故事细节不必赘述。不妨把话题重点放在被人们忽略的一点,即典故中的传媒介质——流水和红叶;囿禁之中的大唐宫女,以河网作朋友圈,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题诗红叶帖子,这个“自媒体”真是靓得很。她们由此实现了与高墙外社交零的突破,不仅找到读者知音,还让自己的诗歌、故事流传千年。“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唐·王建诗)。”君恩不闭东流水,深宫锁得住宫女,挡不住洛水。在傍水而居,利用河网水道运输、文书传递主动脉为邮驿(包括水驿站)的时代,流水,成为传媒载体真是恰当之至。用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话说:“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滕王阁序》),那时的社交有太多偶遇、邂逅的因素。说到流水传信,很自然让人想到源自中世纪的漂流瓶。在交通、通讯封闭狭隘的时代,漂流瓶起到传输不同区域乃至国度间信息文化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又一次全民思想解放,受经济、交通、通讯诸因素影响,社交尚不发达,当时报刊上大都设置征婚启事栏目,而有些情窦初开的浪漫男女也曾投下留有通信地址的漂流瓶于河海之上,期望结得知音寻得良缘,体现了信息闭塞年代人们对表达、沟通的急切愿望。受此启发,而今漂流瓶已进入互联网,百度等平台出现了网络版的漂流瓶,“新漂流瓶”网还专门开了提供浪漫邂逅的“恋爱漂流瓶”平台。作为交友平台,网络漂流瓶的发瓶人与捞瓶人完全陌生,彼此更容易吐露心声,结缘知音。这与御沟传叶何其相似乃尔,可谓异曲同工。秋叶作纸写字,也不是宫女独有。与顾况差不多同时代,还有个国子监广文馆博士郑虔,曾经在长安城南慈恩寺以柿树叶练字写诗作画,被玄宗赞为“郑虔三绝”。(事出唐·李绰《尚书故实》)只可惜,郑虔没有宫女的浪漫,那些本来就是和尚储存用来生火的叶子最终都被塞进灶膛煮粥去了。郑虔乃盛唐著名高士,一代通儒,连诗圣杜甫都称赞他“荥阳冠众儒”、“文传天下口”。若有人于流水上得其柿叶诗书画,不知收藏价值几何。流水、落叶自古被视为无情之物,但经幽怨宫女的成功操作结合,成为奇媒,令人感慨。红叶题诗故事流传不衰,一方面与有着深刻社会历史背景的宫怨主题及佛家天定姻缘思想有关,这是内容;还有一个形式问题,就是红叶题诗洛水流传。-2-唐玄宗开元(-)年间,还有一个短袍传诗的故事。说的是宫女们应诏为边塞守军缝制军袍,一士兵在短袍中发现一诗:“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呵,这简直就是一首征婚诗啊!)这士兵不敢隐瞒,层层上报。李隆基经调查还真找到了这位宫女,不仅没有责杀,反同情赞赏,说:“我与汝结今生缘。”于是这位宫女嫁给了得到诗袍的士兵。依然是无独有偶。唐僖宗时又有宫女作“金锁诗”:“玉烛制袍夜,金刀呵手裁。锁寄千里客,锁心终不开”,和金锁共藏御赐征袍中,被戍边的神策军马真所得。最终,僖宗为他们赐婚结良缘(此二事均出自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这同样是两桩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上阳宫 不难比较,从立意、内涵到艺术水平,袍中诗、金锁诗比前述红叶诗水平更高,尤其金锁诗,因锁寄意,借物言情,构思巧妙,含蓄有言外之义。明代文学家钟惺称赞此诗“锁情锁心字俱奇,奇犹在锁情相寄耳。”但是,同是宫女“发帖”寄情,短袍诗、金锁诗甚至连皇帝都成了忠实读者,其事迹流传演绎程度却远不及红叶传诗。什么原因?还是媒体介质的问题。你想啊,御寒的棉袍、俗气的金锁,哪里比得上流水、红叶的浪漫无忌呢!原本“落叶无语空辞树,流水无情自入池(白居易诗)”,经宫女的离奇、大胆创意,落叶、流水有了比“所谓佳人,在水一方”还要绵绵幽远的情思。同样在唐代,还有一位四川诗人唐球(号山人),一生郁郁不得志,死前将自己不招人待见的诗稿放在一个大瓢里,置江水之上,希望身后结得知音。结果,大瓢漂到新渠,捞得者惊呼:“唐山人瓢也!”(事见《唐诗纪事》)绝望中的唐山人,也是用了有情流水留下一段传世佳话。他的大瓢,离漂流瓶更近一些了。-3- 唐开元年间,王之涣请王昌龄、高适到旗亭喝酒,当时恰好有十几名歇夜伶官也在那里会宴。之涣三人私下约定:看歌伎唱得最多的是谁的诗,以此来证明谁的作品最受欢迎。结果,歌伎们两唱王昌龄诗一唱高适诗。王之涣坐不住了,指着长得最漂亮的一个歌伎说:“要是她不唱我的诗,我就一辈子也不敢同你们吟唱争比高下了。”果然,这位歌伎一开口便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凉州词》起句),三人哈哈大笑。这正是有名的“旗亭会唱”(亦称旗亭赌唱,事出《全唐诗》)。 这个典故,透露了创造亘古绝后奇迹的唐朝诗歌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嘴唱”。唐代印刷业(刻印)尚在初兴中。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那时的文字传播,处在手写传抄方面,当然不存在像今天这样刊登诗歌的《诗刊》《星星》诸般杂志,诗歌的发表传播,除手抄外,最流行的形式之一便是“嘴唱”(鲁迅先生即很欣赏“嘴唱”的诗,认为要比“眼看的”好;当年白居易作诗也追求必使老妪都能诵解),诗之所以也称诗歌,在于其韵律节调生动易唱,也因此更容易被记住,口口相传,得以远播。而身处公共场所的歌伎,无疑是靠“嘴唱”传播诗人作品的生力军。 唐代另一个流行的诗歌传媒是墙壁(包括山石壁),题壁诗是也。题壁诗始自两汉,至唐代骤成风气。仅唐人诗集统计,当时题壁诗的作者即有百数十家。就载体而言,墙壁可真是个好东西,但不是说什么墙都可以题诗。诗壁又有官壁、寺壁、石壁、驿墙壁(邮亭壁)、殿壁、楼壁之分。在这方面,与白居易并称“元白”的元稹可谓最为痴迷,为欣赏题壁诗,他甚至尽日“不离墙下”。他本人也将白居易的诗题于阆州西寺;作为回报,白居易书元稹诗百首合为屏风,正是“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白居易《答微之》) 还是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诗),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诗)。”可见“嘴唱”与题壁在唐代诗歌发表传播的普及。又因为题壁诗多在人群往来密集的公共场所,今人将古诗壁称为诗人们的朋友圈,诗歌即帖子,壁上诸多唱和跟进就是发帖和跟帖了。可惜,这对当时的宫女们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宫内高墙殿壁华丽,别说题诗,在上面写个名字那也是找死啊! -4- 关于唐代女性的诗歌,近代诗词研究名家胡云翼(-)认为:“最大的缺点在无高旷的境界,易流于浅俗。”(《唐诗研究》)他较看好鱼玄机和薛涛,尤以薛涛为高。 说到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的薛涛(-),其实比她的诗声誉更高的是她的“浣花笺”。薛涛一生酷爱红色,在成都时(芳龄20岁),常常一身红裳流连于住所附近的浣花溪边,受无处不见的红色木棉花启示,生出制作红色诗笺的创意。于是,由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制作而成的桃红色诗笺诞生了,又因她“好制小诗”,笺的规制窄小,专门用于题写小诗(这简直与流水、红叶的气息相通了)。薛涛通过题诗小红笺,得以与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诗坛大腕频频交流酬和,不仅朋友圈人气大增,“薛涛笺”也风靡开来,从诗笺到信笺,后来甚至成为官方国札用品。 薛涛画像 薛涛幼年丧父(父亲曾在宫中做官),后沦为歌伎,做“女校书”时又一度红得发紫,还和元稹有过一段热烈却无果的爱情,最终在垂暮之年孤隐于成都。其一生尽管内心悲苦,但比起宫女诗人的命运要好得多。她那有名的小红笺,宫女们怕是见都没见过,更别说在上面题一首小诗了。好在宫里不缺叶子,秋来也是红的,比“浣花笺”不逊颜色,既然没机会贴近元稹白居易们,那就托付流水,发帖去找吧! 我们看唐代流传下来的宫怨诗,男诗人书写较多。前面所述几首宫女作品(一部分),得以流传,可谓珍贵之弥补。按胡云翼先生话说:“既入宫门,必须借制征衣和红叶题诗,始能将哀怨传出,其余不能传到外面而湮没的诗,更不知多少了。”(《唐诗研究》) 红叶题诗、御沟流叶,征袍传诗,宫女们的“朋友圈”虽比不得薛涛,然而,这个圈不大,却能找到知音甚至结下奇缘;这个圈不大,却以空前创意,其涟漪波及千年,拥有粉丝亿万。 .4.9 (图片来自网络)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a.com/mfrpz/4344.html
- 上一篇文章: 北京月子中心十大品牌排行榜
- 下一篇文章: 中药知识必学金银花